- 新战国联盟论坛 (http://newtenka.cn/bbs/index.asp)
-- 『镰仓鹤冈八幡宫』 (http://newtenka.cn/bbs/list.asp?boardid=4)
---- !! (http://newtenka.cn/bbs/dispbbs.asp?boardid=4&id=6434)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4:38:56
-- !!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27:02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4:40:27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4:04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4:42:13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4:20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4:51:40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4:37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4:53:41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4:51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4:55:21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5:05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4:56:41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5:34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4:58:07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5:50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5:01:05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6:05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5:01:57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6:27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0-27 15:02:56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6:53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1-11 22:49:32
-- 太祖4卷,2年(1393癸酉/洪武26年)12月13日(甲申)
镇安君芳雨,上之长子也,性嗜酒,日以痛饮为事,饮烧酒病作而卒。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6-1 0:56:19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1-14 18:23:52
-- 定宗3卷,2年(1400庚辰/建文2年)1月28日(甲午)
放怀安公芳幹于兔山。芳毅、芳幹及靖安公,皆上之母弟也。上无嫡嗣,母弟当为后。益安性醇谨无他,芳幹谓以次当立,然不学狂痴;靖安公英睿夙成,通经达理,开国定社皆其功也,故国人咸归心焉。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6-1 14:41:31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1-16 13:31:32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7:46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1-16 14:00:13
--
阿彌佗彿,功德無量。
主公大可放手寫去,不必先求一早出版。若此時即為出版計,寫的必不得不委曲求全,反失真相;不如不作出版一計,放手寫去,為後人留一真跡。
當然,我們仍然希望這部詳博謹嚴著作,可以早日出版。
-- 发布时间:2007-11-16 23:49:58
-- 定宗3卷,2年(1400庚辰/建文2年)2月1日(丙申)
参赞门下府事河崙等请曰:“梦周之乱,若无靖安公,大事几不成;道传之乱,若无靖安公,亦安有今日乎?且以昨日之事观之,天意人心亦可知也。请立靖安公为世子。”上曰:“卿等之言甚善。”遂命都承旨李文和传旨都堂曰:“大抵国本定,然后众志定。今者之乱,正以国本未定故也。予有称孽子,考其生之日月,未协于期,暧昧难知,且又昏弱,置之于外久矣,向者偶入宫内,今还黜外。且古之圣王虽有嫡嗣,亦择贤而传之。母弟靖安公芳远,开国之初有大勋劳,又于定社之际,吾兄弟四五人得全性命,皆其功也。今命为世子,且令都督内外诸军事。”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6-1 14:13:39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1-17 0:23:45
--
虽然文中不乏勘误之处(已在其他论坛陆续说明),但在国内朝鲜历史资料严重缺乏的前提下能写下如此文章,也实属不易。
(请勿在本论坛讨论文艺作品,请认真阅读置顶章程。 马 编辑)
[此贴子已经被马羽茶水斋于2007-11-18 19:29:52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1-18 11:59:35
--
(请勿在本论坛讨论文艺作品,请认真阅读置顶章程。 马 编辑)
[此贴子已经被马羽茶水斋于2007-11-18 19:18:38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1-18 12:31:16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7:22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2-21 7:24:26
--
说到俄馆播迁, 送隆熙四年德寿宫地图一张, 可见俄馆位置. 当时德寿宫面积比今日大得多, 布局极其杂乱无章, 保留了月山大君私邸时代的特色. 蓝线为今日德寿宫范围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-12-21 7:27:09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7-12-21 7:26:28
--
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untitled.jpg:
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untitled.jpg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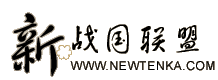
-- 发布时间:2008-2-16 16:14:22
-- 太宗1卷,1年(1401辛巳/建文3年)6月12日(己巳)
帝遣通政寺丞章谨、文渊阁待诏端木礼来锡王命。谨、礼持节至,设山棚结彩,备傩礼百戏。上御纱帽团领,具仪仗鼓吹,出迎于宣义门,百官具公服以从。导至无逸殿,宣诰命:“奉天承运,皇帝诰曰:‘古先哲王之为治,德穷施普,覆育万方。凡厥有邦,无间内外,罔不臣服,爰树君长,俾乂其民人,以藩屏于华夏。朕承大统,师古成宪。咨尔朝鲜权知国事李芳远,袭父兄之传,镇绥兹土,来效职贡,以未受封,祈请勤至。兹庸命尔为朝鲜国王,锡以金印,长兹东土。呜呼!天无常心,惟民是从;民无常戴,惟德是怀。尔其懋德,以承眷佑,孝友于家,忠顺于上,仁惠于下,俾黎民受福,后昆昭式,永辅于中国。啓土建家,匪德莫宜,可不敬哉!’”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6-1 23:17:56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8-2-21 16:17:16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8:12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8-2-21 16:17:59
--
~~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23-2-28 10:08:28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8-3-10 15:33:59
--
以下是引用诹访赖清在2008-2-16 16:14:22的发言:
呵呵,德寿宫平面图上居然还有米国和露国领事馆,莫非是日本绘制的?
呵呵,德寿宫平面图上居然还有米国和露国领事馆,莫非是日本绘制的?
韩帝国时期绘制的。
黑字是原图有的,我用红字重新写了一遍。
韩帝国时期也用汉字,以及“米国”、“露国”等称呼。
原图拽自《朝鲜时代宫阙仪礼运营与建筑形制》,工学博士论文,首尔大学建筑学系,曹在植,2003年8月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3-10 15:34:45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8-3-15 23:21:56
-- 太宗1卷,1年(1401辛巳/建文3年)6月12日(己巳)
上服绛纱袍、远遊冠,受群臣贺。是日,三司右使李稷、总制尹坤等,赍捧礼部咨文而來,各赐鞍马。其咨曰:“建文三年四月十五日,准朝鲜国权署国事李芳远咨,该称:‘亲兄李曔无嗣,令继其后,不期亲兄忽患风疾,委令权袭国事。自念愚庸,不敢承当,辞至再三,兄曔已遣陪臣李詹奏达,不得已于建文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权袭句当,凡有行移只用白头文字。窃念诰命印信理宜申请,差通事判殿中寺事李玄赍咨,同三司右使李稷等赴京,移咨闻奏,乞赐明降施行。’本月十六日晩本部具本,于奉天门奏奉圣旨:‘他既于伦理上无差,忠顺朝廷,恳切来请,诰与印都给赐与他,钦此。’除钦遵差正使通政寺丞章谨、文渊阁待诏端木礼,持节赍捧诰命印章前去本国给赐外,拟合回咨知会,钦遵施行。诰命一道,朝鲜国王金印一颗,四角篆文,并金印池一个,锁匣全。”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6-1 14:43:33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8-3-19 13:34:00
-- 太宗2卷,1年(1401辛巳/建文3年)9月1日(丁亥)
朝廷使臣太仆寺少卿祝孟献、礼部主事陆顒奉敕书来。孟献等率兽医王明、周继至,设山棚结彩,备傩礼百戏,上以冕服率群臣迎于西郊,至议政府宣敕。皇帝手诏曰:“敕朝鲜国王:前使者还,王以中国军兴乏马,特贡三千匹,兹复遣人贡良马、名药、织布诸物,礼意恭顺,朕甚嘉焉。昔周盛时,内有管蔡之乱,而越裳氏万里入贡,成王、周公喜之,其事著于传记,越裳氏之名荣华至今。朕德不逮古,而朝鲜为国视越裳为大,入贡之礼有加,今特遣太仆寺少卿祝孟献、礼部主事陆顒,赐王及父兄、亲戚、陪臣文绮绢各有数,以致嘉劳之怀,至可领也。夫守道者福之所随,违道者殃之所集,天之命也。朕奉天而行,乐与宇内同臻于治,尚其勖之,以绥多福。颁赐国王文绮绢各六匹、药材木香二十斤、丁香三十斤、乳香一十斤、辰砂五斤;前王李旦文绮绢各五匹;前权知国事李曔文绮绢各五匹;別敕颁赐国王亲戚李和、李芳毅等一十三员,每员文绮绢各四匹;陪臣赵浚、李居易等二十四员,每员文绮绢各三匹。”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6-1 14:11:53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8-3-19 13:35:33
-- 太宗3卷,2年(1402壬午/建文4年)2月26日(己卯)
帝遣鸿胪寺行人潘文奎来,锡王冕服,结山棚备傩礼,上率群臣迎于郊,至阙受敕书冕服,出服冕服行礼。其敕书曰:‘敕朝鲜国王李芳远:日者陪臣来朝,屡以冕服为请,事下有司,稽诸古制,以为‘四夷之国,虽大曰子,且朝鲜本郡王爵,宜赐以五章或七章服。’朕惟《春秋》之义,远人能自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今朝鲜固远郡也,而能自进于礼义,不得待以子男礼,且其地逖在海外,非恃中国之宠数,则无以令其臣民。兹特命赐以亲王九章之服,遣使者往谕朕意。呜呼!朕之于王,显宠表饰,无异吾骨肉,所以示亲爱也。王其笃慎忠孝,保乃宠命,世为东藩,以补华夏,称朕意焉。’”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6-1 14:25:36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8-5-22 7:36:28
-- 太宗4卷,2年(1402壬午/建文4年)10月12日(壬戌)
朝廷使臣都察院佥都御史俞士吉、鸿胪寺少卿汪泰、内史温全、杨宁奉诏书至,结山棚,备傩礼、军威,上具冕服,率群臣迎于西郊,至阙宣诏: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:‘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,临御天下垂四十年,薄海內外皆为臣妾。高皇帝弃群臣,建文嗣位,权归奸慝,变乱宪章,戕害骨肉,祸几及朕。于是钦承祖训,不得已而起兵,以清憝恶,赖天地祖宗之灵、将士之力,战胜攻克。然初不欲长驱,始观兵于济南,再逗遛于河北,近驻淮泗,循至京畿,冀其去彼奸回,悔罪改過。不期建文为奸权逼胁,阖宫自焚。诸王大臣、百官万姓,以朕为高皇帝正嫡,合辞劝进,缵承大统。朕以宗庙社稷之重,已于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,大赦天下,改明年为永乐元年,嘉与万方同臻至治。念尔朝鲜,高皇帝时常效职贡,故遣使诏谕,想宜知悉。’”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6-1 23:22:14编辑过]
-- 发布时间:2008-5-29 22:48:28
-- 太宗5卷,3年(1403癸未/永乐1年)4月8日(甲寅)
都指挥高得、通政司左通政赵居任及宦官太监黄俨、曹天宝、本朝宦者朱允端、韩帖木儿等赍诰命印章敕书至,设山棚结彩,备傩礼,上具冕服,率群臣迎于西郊,至阙行礼,受诰命印章。
“奉天承运,皇帝制曰:‘朕惟王者受命,混六合为一家;天道同仁,视万方为一体;所以地无遐迩,人咸景从。我皇考太祖高皇帝,诞膺天命,肇造寰区,薄海内外,悉皆臣顺。尔朝鲜国居东藩,聿先声教,职贡之礼,少有愆违,故在朝廷屡降宠锡。肆朕统御之始,尔李芳远深念皇考之恩,遵承乃父之训,即陈表奏,效职来庭。眷此忠诚,良足嘉尚。兹用命尔为朝鲜国王,锡以印章,永胙茅土。於戏!保国安民,恪守畏天之道;作藩树屏,式谋贻后之规。厥位寔艰,朕言惟允,毋怠毋荒,尔其钦哉!’”
“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芳远:朕惟天有显道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,其应犹影响昭然可畏之甚也。昔我皇考太祖高皇帝,君临华夏,奄有万方,敬天勤民,成功致治。凡日月照临之地,有血气者莫不尊亲。惟朝鲜密迩海隅,声教先被,畏威怀德,效职如常,我皇考式用怀柔,良申赉予。肆朕即位之初,即遣诏谕,尔李芳远果能恭顺天道,念我皇考深恩,即遣陪臣奉表贡献,礼意之勤足有可嘉。今特遣使赉朝鲜国王金印及诰命,使尔用昭宠荣。於戏!惟德顺可以律己,惟敬谨可以格天,毋为谲诈,毋尚浮华,毋作聪明,以废典章,毋纳逋逃,以乖旧训。世守藩邦,乂宁尔土,使东表臣民咸沾福泽,岂不韪欤!故兹敕谕,宜体至怀。”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-6-1 23:26:59编辑过]